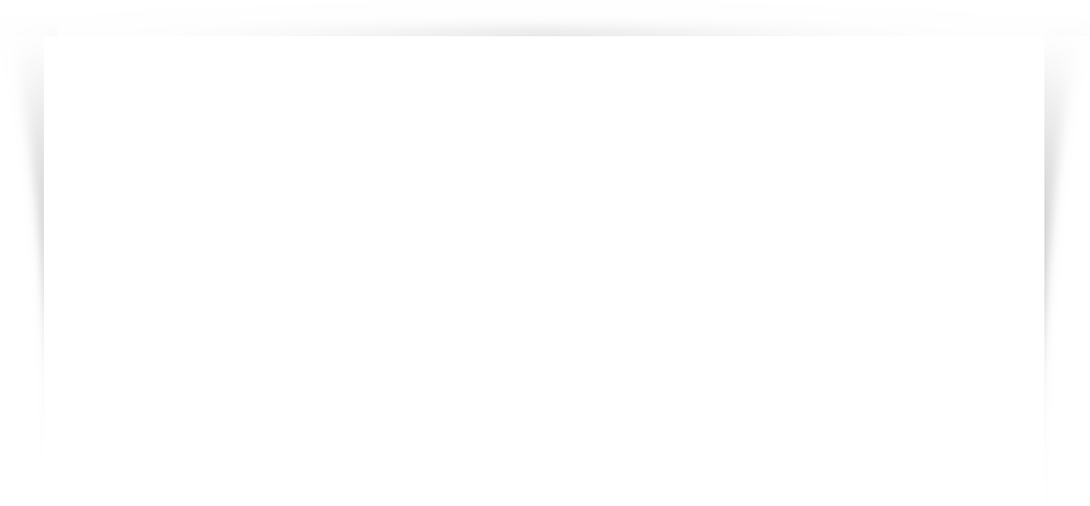
` (moral agency) w 72 Ù - Philosophy Department, CUHK
《荀子》 荀子》的誠及 的誠及自我構建 鄧小虎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 摘要: 《荀子.不苟》有一段論及「君子養心莫善於誠」的文字。自楊倞起的注釋家 大都認為其和《中庸》和《大學》頗有類同。不少學者因此判斷這一段文字和 荀子以「性惡」為核心的思想並不一致,甚至互相衝突。本文並不直接討論 《不苟》的一段文字是否必須假設天生自然的「心善」 ,本文探討的是「君子養 心」到底是怎樣一種活動,並涉及哪些修養工夫。本文以《不苟》一段文字為 基礎,並旁及《荀子》文本其他相關部份,嘗試重構荀子對於道德行動者 (moral agency)的一種理解。本文指出, 「君子養心」是通過「仁義」的修持,使 「心」成為實質的「形之君」 、 「神明之主」 。本文並指出, 「心」之所以能成就 「形之君」 、 「神明之主」 ,很大程度上就繫於「壹」 。這種「壹」 ,既是性情和禮 義的統合,也是自我在當下以及跨時域的統合,其最終目的,即在於構建一個 整全的自我。 關鍵詞:荀子、誠、養心、仁義、自我 “誠"字於《荀子》凡 72 見。1學者已經指出,其中大概一半是作為副詞使 用,意思是“真正地"。2至於其他用例,則大概指稱一種特殊的心靈狀態,暫時 可用“真實"指稱之;即以“誠"指一種“真實"的心靈狀態。本文目的在於釐 清“誠"在荀子思想中的位置,並由此梳理“誠"和《荀子》中理想人格的關係, 最後則希望反思“誠"和個人自我實現的可能關聯。 一、 《不苟 《不苟》 不苟》篇的“ 篇的“誠" 劉殿爵編輯:《荀子逐字索引》(香港:商務印書館,1996),頁 198。值得一提的是,《荀 子.君道》的“將內以固誠,外以拒難",除宋台州本外,諸本及《群書治要》、《韓詩外傳》 皆作“將內以固城"。考察《荀子.君道》的整段文字是“欲治國馭民,調壹上下,將內以固 誠,外以拒難。"另外,《荀子.臣道》提及“內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和“內足使以一 民,外足使以距難"。根據這些語境和文本證據,本文認同王天海先生的判斷,《荀子.君道》 的相關文字應該是“將內以固誠,外以拒難",並且“誠"指“誠信"。王先生的看法見:王 天海:《荀子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 556-7。 佐藤將之:《荀子哲學研究之解構與建構:以中日學者之嘗試與“誠"概念之探討為線索》, 《國立臺灣大學哲學論評》,第 34 期(2007 年 10 月):頁 111。佐藤將之:《掌握變化的道德 ─〈荀子〉“誠"概念的結構》,《漢學研究》,第 27 卷第 4 期(2009 年 12 月):頁 50。 1 2 指稱心靈狀態的“誠"之用例,雖然散見於《荀子》各篇,但最集中(11 次) 也最引人注意的是出現於《不苟》篇的一段文字: 君子養心莫善於誠,致誠則無它事矣。惟仁之為守,惟義之為行。誠心守仁 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變化代 興,謂之天德。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百姓期 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親,不怒而威: 夫此順命,以慎其獨者也。善之為道者,不誠則不獨,不獨則不形,不形則 雖作於心,見於色,出於言,民猶若未從也;雖從必疑。天地為大矣,不誠 則不能化萬物;聖人為知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父子為親矣,不誠則疏; 君上為尊矣,不誠則卑。夫誠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唯所居以 其類至。操之則得之,舍之則失之。操而得之則輕,輕則獨行,獨行而不舍, 則濟矣。濟而材盡,長遷而不反其初,則化矣。 對於這一段文字的詮釋,歷來爭議甚多。在這一節,我們將回顧和整理其中涉及 的不同問題和意見。雖然我們將兼顧訓詁和義理,但主要目的還是在於指出其中 涵含的哲學問題。 對於《荀子.不苟》的這一段“誠論",歷代注釋家很多都留意到其和《禮 記.中庸》和《禮記.大學》的相似。譬如唐人楊倞在注釋“以慎其獨者也"這 一句時,就引用《禮記.中庸》的“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來解釋 “慎其獨"。3清人劉台拱在評論“君子養心莫善於誠"這一句時,也曾指出“誠 者,君子所以成始而成終也。以成始,則《大學》之『誠其意』是也。以成終, 則《中庸》之『至誠無息』是也。"4牟宗三也認為這一段文字“頗類《中庸》 《孟 子》 。此為荀子書中最特別之一段。"牟先生並且指出,這段文字提出“天德" 的說法,是視天為正面的天,和“天生人成"原則中被治的負面天完全不同,也 和《荀子》其他部份不相類。5蔡仁厚基本上認可牟先生的看法,認為此段文字 “非常特殊";其所說的“天"是正面意義的“天",與被治的負面的天“迥不 相侔"。蔡先生並且指出,此段文字所說的“養心",實際上和荀子的思想不一 致,而與荀子思想一致的養心之道,當是《荀子.解蔽》提及的“虛、壹、靜" 的工夫。6 相較於牟蔡兩位先生所代表的《不苟》篇和荀子整體思想不相類、不相符的 意見,另外一些學者則認為《不苟》的這一段文字其實並無和荀子思想不相類的 地方。譬如唐君毅雖然認為這一段文字適足於印證心之性善,但他指出,荀子始 3 4 5 6 王先謙:《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頁 46。 王先謙:《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頁 46。 牟宗三:《名家與荀子》(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79),頁 197。 蔡仁厚:《孔孟荀哲學》(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84),頁 486-89。 終沒有追隨孟子即心言性的進路、沒有主張心善,是因為荀子認為“心之所可" 雖能中理,但亦可不中理,人能守道行道,亦可棄之而不守不行。7唐先生的意思 是,雖然《不苟》一段文字提出了心善的一面,但這和荀子不主心善的立場並不 衝突。因為荀子認為心可善亦可不善,從心實際上表現出善的一面,推導不出心 必然是善的。徐復觀也贊同唐先生這種理解,雖則徐先生並沒有直接論及《不苟》 的這一段文字──徐先生指出:“在荀子的立揚,認為心可以決定向善,也可以 決定不向善。"8唐端正也指出,荀子“所謂誠,不指性而言,但也不指仁義善道 本身,而是指健行不息地守仁守義。故『誠』不著重在致知上,而著重在篤行上。 "9唐先生並且認為,“誠"作為篤行的表現,實際上體現了荀子對人為努力的 重視,因為理想人格恰是通過“誠"這種篤行來達成的。唐先生因此指出,“積 偽就是致誠,致誠就是積偽"。10一如唐端正,韋政通也將“誠"理解為篤行人 格的表現,雖則韋先生並沒有直接評論《不苟》的一段文字。11 其實早在這幾位先生之前,馮友蘭就指出, 《不苟》的“誠"和“慎"恰恰 是和性惡論相一致的。馮先生認為“誠"指真實,“獨"指專一,之所以要真實 專一地追求道德仁義,恰恰因為道德仁義並非人性中所本有,故此需要通過專精 極勤才能使性化於道德仁義。馮先生並且強調,正因為荀子主性惡,所以《不苟》 才提到“長遷而不反其初";這正是主性善者教人復其性的相反。12陳大齊在其 《荀子學說》中雖然沒有直接討論“誠"的問題,但對於《不苟》的“長遷而不 反其初"則有和馮友蘭類似的判斷。陳先生認為,這一句中的“初"的確是指 “性",而“遷"則指遷於偽,意即長遷於偽而不返於性。13換言之,陳先生肯 認了, 《不苟》的一段文字,是對應於荀子思想中的“性惡"和“化性起偽"。 根據“長遷而不反其初"而將《不苟》的一段文字置於性惡的框架下來理解,這 種意見其實還有不少的支持者。譬如趙士林就指出,雖然荀子在《不苟》主張“誠 "有和儒學“內聖"進路有相通之處,但荀子的“誠"強調的是“道德知性"而 非“道德情感"。“道德知性"是通過後天學習所獲得的,恰恰是用以徹底克服 人類與生俱來的本性之惡。14吳樹勤也認為,“誠"指真誠地施行仁義,因為只 有如此才能達致品德完美,而只有品德完美才能改變性惡遷化為善。15 Paul Goldin 留意到《不苟》的“誠"思想和《中庸》相吻合,並且認為《不 苟》的一段文字受到了孟子的影響。不過他認為《不苟》一段文字所依據的依然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性篇》(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84),頁 54。 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頁 242。 唐端正:《荀子述要》,《先秦諸子論叢.續篇》(台北:東大圖書,1983),頁 175。 唐端正:《荀子述要》,頁 176。 韋政通:《荀子與古代哲學》,第二版(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頁 41-42。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頁 221。 陳大齊:《荀子學說》(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社,1989),頁 224。 趙士林:《荀子》(台北:東大圖書,1999),頁 78-9。 吳樹勤:《禮學視時中的荀子人學》(濟南:齊魯書社,2007),頁 90-91。 是性惡的思想。他認為,“誠"指的是人類的自我完“成",即通過依從道及其 體現──禮,人轉化自然之性而發展,並有美好的人生。16Goldin 對於《不苟》 “誠"的理解,主要是將之視為一己育成(self-cultivation)的核心部份。王楷也主 要是從這種道德修養的角度來詮釋《不苟》的“誠"。王楷認為《不苟》的一段 文字和荀子的整體思想並無矛盾。他指出,荀子將“性"視為被治理的對象,而 治理“性"的是“心"這個理性主體。《不苟》的一段文字則強調,“心"本身 也需要持養,而其工夫即在於“誠"。17通過對《不苟》“誠"的考察,王楷意 圖論證,相對於以禮修身,內在的自我反省其實也是荀子思想的重要部份。王楷 認為,無論是孟子還是荀子,其修養工夫都是心行並重,內外兼修的。18 除了“誠"的道德修養層面,佐藤將之亦特別強調“誠"的政治倫理面向。 他在三篇論文中仔細考察了戰國時期“誠"概念的發展,其中兩篇特別以《荀子》 為核心,探究《荀子》“誠"思想在戰國思想的地位和影響。19佐藤將之認為, 《荀子.不苟》的“誠論"無法在“性惡"和“天人之分"的框架下得到恰當理 解,其實際上代表了荀子思想中另一種形態的“天人關係論"。他認為《不苟》 的一段文字受到了《孟子》 、簡帛《五行》 、 《莊子》等諸文本的影響,其主旨在 於指出“誠"是呈現統治者道德倫理的最高方法,並且這種“誠"的顯現過程被 稱之為“天德"。為了調和荀子思想中的“性惡"和帶有性善蘊意的“誠"論, 佐藤先生指出,“誠"在《不苟》中被視為聖人的屬性,而非達致聖人的方法; 並且荀子思想包含了兩種不同的工夫理論:“誠"是“積善"工夫的基礎,而 “性惡"則是“由禮"工夫的基礎。20在另一篇論文中,佐藤將之進一步指出, 荀子的“誠"概念依據的是戰國中後期相當重要的“變化論",而且以“誠"為 核心的荀子倫理思想,和《禮記.中庸》後半部的“誠"學說有共同的理論立論。 21佐藤先生特別強調,他並不否定從“性惡"觀點來探討荀子思想中“化性"的 意義,但他認為,“誠"概念及相關的“變化"觀能夠為“化性"如何可能提供 理論基礎。22 16 Paul Goldin, Rituals of the Way: The Philosophy of Xunzi (Chicago and La Salle, Ill.: Open Court, 1999) 19-20. 17 2009 4 64-71 36 11 2009 11 ): 4358 2011 18 217, 248 王楷:《荀子誠論發微》,《中國哲學史》, 年第 期,頁 ;以及王楷:《君子養心莫 善於誠:荀子誠論的精神修持意蘊》,《哲學與文化》第 卷第 期( 年 月 頁 。這兩篇文章基本上是一樣的,並且是王楷專書的一章。相關專書是王楷:《天然與修為─荀 子道德哲學的精神》(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王楷:《天然與修為─荀子道德哲學的精神》,頁 。 佐藤將之:《戰國時代“誠"概念的形成與意義:以〈孟子〉、〈莊子〉、〈呂氏春秋〉為中 心》,《清華學報》,新 35 卷第 2 期(2005 年 12 月):頁 215-244;佐藤將之:《〈荀子哲學研究之 解構與建構:以中日學者之嘗試與“誠"概念之探討為線索〉》,《國立臺灣大學哲學論評》,第 34 期(2007 年 10 月):頁 87-128;佐藤將之: 《掌握變化的道德─〈荀子〉“誠"概念的結 構》,《漢學研究》,第 27 卷第 4 期(2009 年 12 月):頁 35-60。 佐藤將之:《荀子哲學研究之解構與建構》,頁 115-119。 佐藤將之:《掌握變化的道德─〈荀子〉“誠"概念的結構》,頁 36。 佐藤將之:《掌握變化的道德─〈荀子〉“誠"概念的結構》,頁 47。 19 20 21 22 以上各位學者對於《荀子.不苟》“誠"思想的理解,大體上可以歸納為三 種立場。其一,部份學者認為《不苟》的“誠論"和荀子以“性惡"為代表的思 想體系不相洽,反而更接近《孟子》 、 《中庸》的性善思想。持這種意見的代表有 牟宗三和蔡仁厚。其二,另一些學者則一方面承認《不苟》的“誠論"體現了“心 "善的一面,另一方面則認為這種“心善"的看法其實和“性惡"並不相衝突。 他們傾向認為《不苟》的“誠論"代表了另一階段或者另一層面的修養工夫。佐 藤將之和王楷可以視之為此類立場的代表,唐君毅和徐復觀應該也屬於這種立場。 其三,其他學者則傾向從“性惡"的角度來詮釋《不苟》的“誠論",並認為其 恰恰是“性惡"思想體系不可或缺的一環。持這種立揚的有馮友蘭、唐端正、Paul Goldin、趙士林、吳樹勤等人,韋政通應該也屬於這種立場。當然,這三種立場 只是一種籠統的劃分,許多學者實際的立場比我們在這裡所歸納的要複雜的多。 我們做出這種劃分,主要是為了顯示理解《不苟》“誠論"的三個方向:將之和 荀子思想相切割;視之為荀子思想的一部份,但相對獨立於“性惡"體系;還是 視之為“性惡"體系的重要部份。 本文的立場更傾向於第三種方向,即認為《不苟》“誠論"和“性惡"思想 是相輔相成的。不過,與其說《不苟》“誠論"是“性惡"體系的一部份,不如 說“誠論"和“性惡"各自是荀子思想的構成部份。之所以如此修正我們的表述 是緣於兩點考慮:其一,“性惡"的確切意涵仍然有相當爭議。並且無論“性惡 "的確切意涵為何,“性惡"無論是在《荀子》的文本中還是在後人的論述中, 往往都只是一個簡化的標籤,為的只是方便陳述一套實際上相當複雜的思想體系。 23因此,比較恰當的說法應該是“以性惡為代表的荀子思想"。那麼我們可以說, 《不苟》“誠論"是以“性惡"為代表的荀子思想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其二,之 所以強調“誠論"和“性惡"的緊密關係,是基於一個方法論考量:即在相反證 據出現之前,我們應該將《荀子》文本視為一個整體,並通過詮釋和分析,盡量 整理出一套完整圓融的思想體系,以顯示其獨特的思想、哲學旨趣。在將《不苟》 “誠論"視之為荀子思想的一部份這一方面,本文(以及第三種立場)其實和第 二種立場並無差異,不過本文更傾向於論述《不苟》“誠論"乃至《荀子》文本 各處的“誠"觀念和荀子思想其他部份的關係。 我們可以基於這種考量,從新審視《不苟》“誠論"的一段文字。我們可以 看到,這一段討論“誠"的文字,其出發點是“君子養心"。實際上, 《荀子. 不苟》接近四分之三的篇幅,都是對於“君子"各個方面的討論。“誠論"的一 23 和 都提到了這一點。參見 A. C. Graham A.S. Cua A. C. Graham, “The Background of the Mencian Theory of Human Nature,” Studies in Chinese Philosophy and Philosophical Literature (Singapor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Philosophies, 1986) 57.A. C. Graham, Disputers of the Tao: Philosophical Argument in Ancient China(Chicago and La Salle, Illinois: Open Court, 1989) 250-1. A. S. Cua, “The Conceptual Aspect of Hsun-Tzu’s Philosophy of Human Nature,”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27 (1977): 374. 段文字,涉及的是“君子養心"的問題;針對這個問題,荀子提出了“誠"這個 觀念,並指出其實質就是“守仁"和“行義",而其成果則是“化"和“變"。 然則,“誠"在這一段文字中其實是和至少四個/組觀念相聯繫:“君子"、“養 心"、“仁"和“義"、“化"和“變"。 我們認為,由“士"到“君子"的轉變,其關鍵在於從行為層面上升到心靈 層面,即不僅僅著眼於外在行為,而是更著意於行為背後的義理。而從“君子" 到“聖人"的轉變,其關鍵則在於對於義理是否有全面透徹的瞭解,即是否能 “知通統類",並能以此指導一切的言行舉止。或許我們可以就此初步認為,“誠 "就是成就“君子"並步向聖人的一種修養工夫,而其關鍵則在於使人“篤志"、 “安行",並進而“明知"義理、通曉“統類"。 荀子認為學者應該“全之盡之",而達致“全"“粹"的一個重要面向就是 “使心非是無欲慮也"。24能夠做到“心非是無欲慮也",其實就表示“心"思 慮的對象全然是正理正道。這種境界很可能就是《不苟》“誠論"所提到的“唯 仁之為守,唯義之為行",以及“誠心守仁"和“誠心行義"──即專注真實地 思慮並踐行仁義,而不會受違反仁義的事物影響。 《荀子.解蔽》曾指出,“誠 心"和“心術"本身並不保證善,所以“誠心"追求的對象,以及“心術"的內 容就顯得特別重要。因此, 《解蔽》也提出了“知道"的重要性,並述及“知道 "、“可道"乃至“守道以禁非道"的三個階段。我們推論,“虛壹而靜"是“知 道"的工夫,“心之所可中理"是“可道"的工夫,而《不苟》“誠論"則是“守 道以禁非道"的工夫。“養心"顯然和“道"有密切的關係。《解蔽》仔細論述 了“心"和“道"的關係,指出了“心"“自禁"、“自使"的特質,並提出如 何以“道"指導“心"的運作。後者包括了以“道"為“類",統攝萬事萬物, 並能由“彊"、“忍"、“危"而達致“道心之微"的境界。25簡言之,就是以 “道"為“壹",並能“好"之、“樂"之。荀子曾論及“治氣養心之術",其 總結是“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要得師,莫神一好。夫是之謂治氣養心 之術也。"26其中“莫神一好",指的應該正是“一好"所能帶來的“神明"之 效。27整體而言,我們可以看到“心"、“道"的論述和《不苟》“誠論"有密 切關聯。 另一方面,我們認為“仁義之統"是“先王之道"的實質,而“禮義"則是 《荀子.勸學》。 《荀子.解蔽》在討論“彊"、“忍"、“危"、“微"四種狀態之前,曾引《道經》曰: “人心之危,道心之微。" 《荀子.修身》。 《韓詩外傳.卷二》有類同的一段文字,其中提到“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優得 師,莫慎一好。"不過其接下來卻提到“好一則博,博則精,精則神,神則化。"然則“一好 "最終的成果仍然是“神"和“化"。 24 25 26 27 實現“先王之道"和“仁義"的途徑。 “聖人"不過就是“為仁義法正"之人。 要做到這一點,“塗之人"必須進行“全之盡之"的為學過程。即立下專注堅定 的志向,刻苦學習和施行,思索其間的義理,並最終掌握“仁義法正"的統類。 這種全盡之學,從心靈層面的修養而言,即可稱之為“誠"。我們認為,“化" 和“變"其實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縱然兩者有密切的關係。“化"可以指“化性 "或者“化人"。“化性"是轉化人的自然情性和情欲,使之符合禮義法度;“化 人"是轉化人民百姓,使之安於良好的社會政治秩序,並最終能有群居和一的生 活。其實“化人"的基礎也是“化性",不過“化性"側重於道德倫理的轉化, “化人"則側重於強調這種轉化在社會政治方面的表現。 《不苟》“誠論"所說 的“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描述的正是真誠依從“仁"而有的 “化性"乃至“化人"的成果。“誠心守仁"其實就是“伏術為學"、“積善而 不息",當“學"的效果達致“形乎動靜"的“全盡"之境,乃能有“神明"的 化育之功。至於“變",指的是因為知“理"、“明"“理",所以能夠“以義 變應"。“以義變應"為的是根據不同時局形勢,曲得其宜地以“禮義"實踐 “仁義"之道。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掌握“統類",也就是“道"和“仁義" 之“理"。“知通統類"就是“明",就能“變應"和“應變"。“守仁"的“化 "因此是體,“行義"的“變"則是實踐。兩者的互相構成應該也就類近於荀子 所說的“夫道者體常而盡變"。28兩者相結合,也就是“全盡"之學,乃能“長 遷而不反其初"。這也就是荀子所說的“君子之學如蛻,幡然遷之。"29 可以看到,“君子"、“養心"、“仁義"和“化"、“變"這四組概念都 和有“誠"有緊密的關聯,大致上可以視之為同一個理論體系的不同面向。30我 們可用“化性起偽"來稱呼荀子的這個理論體系──即人通過學習、思慮和實踐 “禮義",掌握“道"和“仁義",從而能轉化自然情性,成為君子乃至聖人。 這是一個“注錯習俗"、“積善成德"的過程。也是“心"“知道"、“可道" 並“守道"的過程。 二、誠和真實 我們之前提到,可以將“誠"視為一種“真實"的心靈狀態。然則這到底是 怎樣一種“真實"?我們認為,“誠"是一種內在修養工夫,其重點在於“心" 和“志意"的持守。“誠"作為一種“真實"的心靈狀態,指的是“心"真實地 接納“道"為一貫的指導原則,並奉行持守其實質內容“仁義",因此能在“志 意"上固守“仁義",並在“身行"方面實踐“仁義",從而做到表裡如一、內 《荀子.解蔽》。 《荀子.不略》。 以上本文簡略概括了“君子"、“養心"、“仁義"和“化"、“變"這四組概念和“誠" 的關係。相關的文本分析,可以參見鄧小虎:《荀子的為己之學:從性惡到養心以誠》(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預計 2015 年)第七及第八章。 28 29 30 外貫通。 以這種理解從新審視《不苟》“誠論",我們乃能進一步理解何以荀子說“君 子養心莫善於誠,致誠則無它事矣。"既然“誠"指的是真實地接納“道"及 “仁義",並使之成為身心如一的指導原則,那麼就難怪荀子說“莫善於誠"和 “無它事"了。因為“誠"正是使得“心"“壹於道"的修養工夫。“誠論"同 時提到“唯仁之為守,唯義之為行",這也印證了“仁義"的確是“心"所需要 真實奉行持守的對象;因為“仁義"正是“先王之道"的實質內容,而表裡如一 地接納實踐“仁義",恰恰是“壹於道"的體現。至於“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 神則能化矣。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說的則是“聖人"掌握了 “仁義之統"後,所能有的神明化變之功。“形"和“神"強調的是“化性"乃 至“化萬民"的功效,“理"和“明"則強調對於“道"和“仁義"的義理的理 解,因此能針對不同的情況形勢“應變無窮"。至於“誠論"接下來所說的“天 德",則是對“君子至德"的類比,一如《堯問》將“執一無失"類比於“天地 "、“行微無怠"類比於“日月"。 “誠論"接著提到“夫此順命,以慎其獨者也。"楊倞認為“順命"指“人 所以順命……人亦不違之",羅焌也認同“順命"指“人懷君子之德,畏君子之 威,皆順其命也"。不過也有相當多注釋家認為“順命"指“順天地四時之命"、 “效天之明命"。31“順命"在《荀子》僅三見,除了《不苟》一例外, 《王制》 提到“使百姓順命",《議兵》則提到“王者之軍制"要求“聞鼓聲而進,聞金 聲而退,順命為上,有功次之",後兩例“順命"都是指順從上位者之命令。另 外《榮辱》也曾提到“上則能順天子之命"。這樣看來,應該是楊倞的理解比較 合理:“順命"指百姓、萬民“順"君子或聖人之“命"。而且“誠論"下文提 到“不誠則不獨,不獨則不形",將“獨"視為“誠"和“形"之間的關聯概念, 其主旨在於說明只有“誠"、“獨"、“形"方能使民眾無懷疑地順從。這也可 間接說明,上文的“順命"應該就是下文的“從"。 至於“獨",楊倞援引《禮記.中庸》的“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 所不聞"以解“慎其獨",認為“獨"指人所不睹、人所不聞。郝懿行雖然不贊 成以“謹"解“慎"、認為“慎"當訓為“誠",但同意“獨"指人之所不見。 32不過自從馬王堆漢帛《五行》及郭店楚簡《五行》相繼出土後,多位學者已經 先後指出,“慎獨"之“獨"並非指獨居,而是指“心"及其地位狀態,特別指 “心"的獨立專注和“心"的主宰義。33竹簡《五行》和帛書《五行》都提到“淑 楊倞及各家注釋,參見王天海:《荀子校釋》105-6。 楊氏及郝氏注釋,參見王先謙:《荀子集解》,頁 46-7。 譬如,丁四新:《略論郭店楚簡〈五行〉思想》,《孔子研究》2000 年第 3 期,頁 50-57;梁 濤:《郭店楚簡與君子慎獨》,《文化中國》第 8 卷第 3 期(2001 年 9 月),頁 48-53;廖名春: 《“慎獨"本義新證》,《學術月刊》2004 年 8 月,頁 48-53;陳來:《“慎獨"與帛書〈五行〉 31 32 33 人君子,其儀一兮。能為一,然後能為君子。君子慎其獨也。"《勸學》同樣引 用了《詩.曹風.鳲鳩》的“淑人君子,其儀一兮"來強調“故君子結於一也"。 雖然《五行》篇被普遍認為是思孟學派的作品,並且很可能是《非十二子》中批 評子思孟軻所提到的“五行",34可是至少在強調“一"這一點上, 《五行》和《荀 子》是相同的。帛書《五行》除了正文之外尚有解說,其中對於“慎其獨"的解 說,提到“舍夫五而慎其心"和“獨也者,舍體也",而且另一部份的解說也提 到“舍其體而獨其心"。根據這些解說,“慎其獨"指認真對待“心"的獨特地 位,特別是“心"對於身體五官的主宰地位。35荀子也曾提及“心居中虛,以治 五官",36以及“形不勝心";37亦曾以四肢和心的關係來形容天子和民眾:“故 天子……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如四胑之從心,夫是之謂大形。"38這樣 看來,雖然《荀子》文本並沒有正面解說“獨"的義涵,但將《不苟》“誠論" 的“獨"理解為“獨其心",至少在義理上是站得住腳的。如果我們接受“獨" 即指專注於“心"、確認“心"對於形體的主宰和掌控,那麼“不誠則不獨,不 獨則不形"的意思應該就是:只有真實地接納、認可以“仁義"為實質內容的 “道",“心"才能“壹於道";而只有當“心"“壹於道"之後,才能確定“心 "對於形體的主宰;當“心"依於“道"而主導“形",就能做到內外貫通、表 裡如一,乃能“形乎動靜"、“形於四海",並因而有神妙的化育之功。39 “誠論"近結尾處說到“操之則得之,舍之則失之。操而得之則輕,輕則獨 行,獨行而不舍,則濟矣。"“操之則得之,舍之則失之"指的應該就是“在我 者"的一己道德修養,這種自我道德修養,能帶來“輕"這種功效。“輕",楊 倞認為是“易舉"之義,猶如《詩.大雅.烝民》所說的“德輶如毛";王天海 則認為應該是指“身心輕鬆"。40不過,荀子曾提及“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 則輕王公;內省而外物輕矣。傳曰: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此之謂矣。"41“輕 "是“獨"的條件,既然“獨"指專注於“心",則“輕"就應該指能使人專注 於“心"的條件;那麼,“輕"外物恰恰是一種合理的詮釋──“輕"外物正和 “內省"、“道義重"和“志意修"相關聯,而後三者也恰可視為“養心"的工 思想》,《中國哲學史》,2008 年第 1 期,頁 5-12。 關於思孟學派和《五行》篇的關係,學者論述甚多,譬如龐樸:《竹帛五行篇與思孟五行 說》,《本世紀出土思想文獻與中國古典哲學研究論文集》上冊,陳福濱編(新莊,台灣:輔仁 大學出版社,1999 年),頁 51-62;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頁 78;梁濤:《郭店竹簡與思孟學派》(北京: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年)。 陳來對此亦有解說,參見陳來:《“慎獨"與帛書〈五行〉思想》,頁 5-7。 《荀子.天論》。 《荀子.非相》。 《荀子.君道》。 《荀子.樂論》也提到“故人不能無樂,樂則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 靜、性術之變盡是矣。故人不能不樂,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為道,則不能無亂。"這恰恰是 從另一方面說明了“道"對“形乎動靜"的重要。 楊倞及王天海注釋,參見王天海:《荀子校釋》,頁 107。 《荀子.修身》。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夫和境界。另外, 《修身》提到“君子役物",而《正名》也提到“重己役物" 及其反面“以己為物役";而“重己"正是對於“在我者"的重視。所以“誠論 "所說的,應該就是重視一己的道德修養,使得自身不受外物牽累,而能肯認、 專注於“心"。專注於“心"而“不舍",就最終能完成一己及他人的道德轉化。 這種道德修化就是“誠論"最後所說的“濟而材盡,長遷而不反其初,則化矣。 "即轉化自然情性的表達之“狀",使之和“禮義"相結合,使得“情文俱盡", 42以達成“性偽合而天下治"。43 我們可以看到《不苟》“誠論"用語雖然近似於《中庸》 、 《大學》乃至《孟 子》關於“誠"的文句,但“誠論"涉及的概念和論證其實在《荀子》文本各處 多有提及。我們認為,“誠論"述及的是“君子"邁向“聖人"的修養工夫,其 關鍵在於使“心"真實接受“道"的實質內容“仁義",使“心"“壹於道"。 要做到真實接受和踐行“仁義",就必須掌握“仁義之統"、“明知"其“類", 如是也就能有“神明"的“化"、“變"之功。“心"“壹於道"同時也是表裡 合一、內外貫通、知行並重;能如此就能由內而外地轉化自然情性的表現之狀, 使之和“禮義"相結合,以達致“性偽合"並成就“全盡"之學。另外,“誠論 "應該就是“心"的“守道以禁非道",其和“虛壹而靜"的“知道"以及“心 之所可"的“可道",共同構成了荀子“化性起偽"的修養工夫。 三、仁義和心之主宰 上文已經提到,“誠"這種心靈狀態的“真實",就表現在“真實"地接納 “道"及其實質內容“仁義",並以之指導身行,使得內外貫通、表裡如一。可 是,我們尚未認真探討,這種“真實"的接納、認受乃至實踐,何以能有內外貫 通、表裡如一的“壹"和“貫"的作用。這裡涉及幾個問題:第一,這種“真實 "的接納和認受,在什麼意義上是“真實"的?第二,這種“真實"何以能使人 內外貫通、表裡如一?第三,這種“真實"到底有何重要性? 要探討怎樣謂之“真實"的接納和認受,我們需要先確立相關的衡量標準, 即根據什麼標準我們可以說某些接納或認受是“真實"或“不真實"。譬如我們 對外在世界的認識是否真確,其標準即在於外在世界本身的狀態──如果我將身 前的“寢石"誤認為“伏虎",我的認識是非真確的,因為在我身前的並非“伏 《荀子.禮論》提到“凡禮,始乎梲,成乎文,終乎悅校。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 代勝;其下復情以歸大一也。"“情文俱盡"即是“禮"“至備"的表現。 《荀子.禮論》提到“性者,本始材朴也;偽者,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偽之無所加,無偽則 性不能自美。性偽合,然後聖人之名,一天下之功於是就也。故曰: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接 而變化起,性偽合而天下治。"“材"也可指稱“性",然則“材盡"也可以理解為《禮記. 中庸》的“盡其性"及“盡人之性"。不過,荀子大概會強調,“盡其性"並非“性"的自然 表現,而是“性偽合"所帶來的成果。 42 43 虎"而是“寢石"。44對於心靈狀態而言,“真實"的標準是什麼呢?一個可能 的答案就是心靈狀態的本來面貌。 《禮記.大學》的“毋自欺"可以視之為這樣 一種標準。 《大學》認為,如實地“惡惡臭"、“好好色",就是“誠其意"。 實際上,這也是我們日常生活中所理解的“真誠",即如實、不作假地表露自己 的心意想法,既不自欺,亦不欺人。不過《不苟》“誠論"以及《荀子》文本所 述的“誠"並不僅指一時一地的不自欺,而是指持續不懈地接納、實踐“仁義" 乃至“禮義"。而且“毋自欺"單獨而言只是形式條件;小人如果放肆地表露其 小人的心意和行徑,其實也算得上“毋自欺",但荀子決不會以“誠"形容之。 恰恰相反,荀子認為只有君子才能“誠"。然則在形式條件之外,“誠"同時要 求相應的實質內容。 《不苟》“誠論"的主題是“君子養心"。然則“誠"這種“真實"的心靈 狀態,以及接納認受“仁義"之所以是“真實",都應該是針對“心"而言的。 荀子曾指出,“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45這一段 文字描述的,很可能就是荀子所認為的“心"的本來狀態;這種本來狀態也應該 同時是“心"的理想狀態。上文參考漢帛《五行》的解說,將“慎其獨"理解為 認真對待“心"的獨特地位,特別是“心"對於身體五官的主宰地位。“形之君 "指的恰就是“心"對於形體的主宰。我們亦曾指出“誠論"之中“輕則獨行" 的“輕"應該指“輕"外物,並且提及了“重己役物"和“以己為物役"。在這 裡我們可以進一步解釋“重己役物"或“以己為物役"和“心者,形之君"的關 係。 我們之前提到,“輕"外物可以使人專注於“心",所以是“輕則獨行"。 其實相反的情況也同樣成立,所以荀子也曾指出“重物"會令“心憂恐"。46雖 然荀子沒有直接說“心憂恐"就等於“心"不是“形之君"、不是“神明之主", 但我們從《正名》相關章節的上下文來看,卻能夠推論“重物"正能使得“心" 失其正,並喪失其主宰形體和一己生命的功能:荀子在“心憂恐"之後,提到“欲 養其樂而攻其心,欲養其名而亂其行",並最終總結“夫是之謂以己為物役矣。 "“攻其心"、“亂其行"恰恰表明“心"受到攻擊傷害,並且“心"無力主宰 行為而使得舉止散亂。“以己為物役"更清楚指出,一己受到外物役使而無法安 頓生命。“己"雖然並不等同於“心",但“心"作為“神明之主",顯然是和 “己"有密切關係。我們可以做以下的論述:“己"是相對於外物和他人的“我 "這個整體,“己"包括了“我"的心靈和肉體;“心"既然是“形"和“五官 "的“君",47則其顯然負責主導、控制五官形體,並因而是“己"的內在主宰。 《荀子.解蔽》即提到“冥冥而行者,見寢石以為伏虎也,見植林以為後人也:冥冥蔽其明 也。" 《荀子.解蔽》。 《荀子.正名》。 《荀子.天論》也提到“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 44 45 46 47 那麼,我們可以將“心"和“己"的關係表述為以下兩條命題: 一、心是己的主宰。 二、若且心主宰,則己為自身主宰。 當“以己為物役"時,“己"既然淪為外物的奴役,則顯然“己"已經不是自身 主宰。根據“逆斷律"(modus tollens)的推論原則,否定後項可以推導致否定前項; 所以從“己"不是自身主宰,我們可以推導致心不是主宰。換言之,“以己為物 役"正是“心"“形之君"、“神明之主"的否定。“重己役物"和“君子役物 "都表示“己"為自身主宰。從這一點我們尚不能邏輯地推導致“心主宰",因 為肯定後項不能推導致肯定前項。可是形體五官並不能帶來“己"的主宰,實際 上只有“心"的主宰能導致“己"為自身主宰。因此“心"和“己"的關係應該 是: 二*、若且唯若心主宰,則己為自身主宰。 通過二*這個命題,我們想表達的是“心主宰"和“己為自身主宰"互為充份必 要條件的關係。既然“重己役物"和“君子役物"都薀涵了“心主宰",那麼促 成“君子役物"的條件和原因,顯然也就能促成“心主宰"。“君子役物"的條 件是“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內省而外物輕矣。"48“志意修"、 “道義重"和“內省"都是道德修養工夫,對荀子而言其實質內容也就是對“仁 義"和“禮義"的持守實踐。也就是說,接納、認受、實踐“仁義",可以使人 “重己役物",以“心"主宰“形"和外物,並掌握一己的生命。因此,我們可 以說接納認受“仁義"是“誠",是“真實",因為其使得“心"能夠以“真實 "的狀態主宰生命。 以上的論證,只是使我們初步理解了何以接納認受“仁義"是“真實"的表 現──因為“仁義"能促成“心"的主宰。可是我們尚需要進一步探討,何以 “仁義"能促成“心"的主宰,並維繫“真實"的心靈狀態──即,“仁義"到 底能產生何種作用,從而能促成和維持“心"對於一己生命的主宰? 上面提到,“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是“心" 的本來狀態。如果“心"並不會偏離其本來狀態,或者在一般情況下不會失去其 “君"和“主"的地位,那麼我們大概不需要“仁義"乃至“誠"。不過,荀子 的確認為,“心"很容易就會失去其主宰地位。所以荀子一方面說,“人無師無 法,則其心正其口腹也",指出人如果沒有師長和法則的引導,其“心"就只會 48 《荀子.修身》。 順從口腹之欲,“亦呥呥而嚼,鄉鄉而飽已矣"。49換言之,“人無師無法", “心"就會被形體所驅使,其“形之君"、“神明之主"的地位就變得只是虛設, 而並無實質的主宰地位。另一方面,荀子也說“人之生固小人,無師無法則唯利 50 51 之見耳。" 荀子曾指出“小人役於物", 那麼“人之生固小人"就意味人生來 就有傾向“以己為物役"。這裡我們需要強調,“人之生固小人"和“心者,形 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這種“心"的本來狀態並無矛盾。這是因為“心"作為 “君"和“主"可以有形式地位和實質地位的區分。“形之君"、“神明之主" 這種形式地位是不會改變的,但“心"是否能有實質的“君"和“主"的主宰地 位,則正正視乎人是否遵從師法禮義、是否努力於道德修養以成為君子。52 為了進一步解釋“心"作為虛設的“君"、“主"和實質的主宰之間的區分, 我們需要檢視《荀子》中“可"這個概念。荀子曾指出“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 也;求者從所可,所受乎心也。"53“欲不待可得"表示“欲"之有無並不視乎 其是否“可得";54“所可"指的正是“心之所可",也是求取情欲滿足者所遵 從的指引。在這一段引文之後,荀子亦曾說“以所欲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 免也。以為可而道之,知所必出也。"55這一則文本清楚地說明了,不但“欲" 之有無,甚至對於“所欲"的求取,都是自然而有,並且無法避免的。也就是說, 欲望的出現,以及對於欲望目標的渴求,都是自然性情不可避免的表現。不過, “知"可以判斷這些欲求是否“可",並可以引導應該如何求取。這裡所說的 “知",其實就是“心"的功能。因為荀子曾說“心有徵知……五官簿之而不知 56 ", 即五官只能收集相對應的訊息如形色、聲音、味道、香臭等,卻不能“知 ",而“知"是“心"的能力。另一方面,在“以為可而道之,知所必出也"之 後,荀子描述了“欲"可以“進盡"或“節求"等情況,並總結“道"就是或 “近盡"或“節求"的標準。而荀子亦曾自問自答:“人何以知道?曰:心。" 57 結合這兩則引文,我們亦可看出“知"正是出自於“心",而“以為可"亦即 “心之所可"。“求者從所可,所受乎心也"以及“以為可而道之,知所必出也 ",都表明“可"是“心"必然有的一種功能;然而這兩則引文都沒有指出,“心 兩則引文皆出於《荀子.榮辱》。 《荀子.榮辱》。 《荀子.修身》。 聖人在出生時也是小人,但其時並未有師法禮義,然則聖人又如何擺脫小人的狀態,最終成 為聖人?荀子的答案是“積思慮,習偽故"。《荀子.性惡》所說的“聖人積思慮、習偽故,以 生禮義而起法度",既可理解為聖人生成“禮義法度"的過程,也可以理解為聖人通過思慮積 偽來進行道德修養,最終成就聖人的過程。所以嚴格而言,“師法"代表的是一種超越當下情 欲、以心的思慮來指導性情的狀態。 《荀子.正名》。 關於這一點,郭嵩燾解釋得甚為清楚:“人生而有欲,不待其可得而後欲之,此根於性者 也。"見王天海:《荀子校釋》,頁 921。 《荀子.正名》。 《荀子.正名》。 《荀子.解蔽》。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之所可"必然能成功主導情欲。相反,荀子指出“心之所可"有“中理"或“失 58 理"的情況。 荀子亦曾說“人倫並處,同求而異道,同欲而異知,生也。皆有 59 可也,知愚同;所可異也,知愚分。" 荀子認為人雖然有共同的追求,卻採取 了不同的方法,所以他指出無論智者愚者都有“可",但“所可"的差異,卻表 現了智愚的區分。“皆有可也"印證了我們以上所說的,“可"是“心"的必然 表現,即人人皆有“心之所可"。可是,“心之所可"是否能發揮其指導“情之 所欲"的功能,卻不必然。根據這一系列的文本證據,我們有理由相信,“心之 所可"展示的只是“心"對於“情之所欲"位階、名目上的主導。“心之所可" 是否能真正主導情欲、是否能成功地“道欲",就決定了“心"是否有實質的主 宰地位,也決定了“心"是否能實現其“真實"狀態。 四、整全的自我 我們之前曾指出,“己"是相對於外物和他人的“我"這個整體,並包括了 “我"的心靈和肉體。在一時一地,“己"或“自我"一般都能夠和他人相區別。 即便是失憶人士也能夠問“我是誰?"然而,當失憶人士問“我是誰?"時,他 顯然追求更實質的自我內容而不是一個類似於“你是你"或“我是我"的形式 答案。如果我們不假設獨立靈魂的存在,從一種自然主義(即契合於現代自然科 學的世界觀)的角度來看,是什麼使得各種經歷、記憶、人生片斷共同構成某一 “自我"的實質內容呢?我們並不意圖為這個形上學難題提供全面答案。60我們 想做的,只是從倫理學的角度,嘗試重構荀子對此的可能答案。我們將指出,“誠 "所涵蓋的“守仁"、“行義",以及其中“壹"和“貫"的作用,其重點即在 於建構一個整全的自我。 我們已經提到“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61我 們曾指出,“心"是否實質的“君"、“主",即是否實質主宰,其實是和“己 "是否不受役使、是否自主,有互相構成的關係。人在可能的情況下,總是不希 62 望受奴役,總是希望能夠自主、能夠掌握自己的人生。 既然人不希望“以己為 物役",那麼能夠使人“重己役物",能夠促成“心"為主宰、為實質的“君" 和“主"的種種規範,就是人所應該遵從實踐的。荀子在《不苟》“誠論"指出 《荀子.正名》提到“心之所可中理,則欲雖多,奚傷於治?"和“心之所可失理,則欲雖 寡,奚止於亂?" 《荀子.富國》。 關於“人身同一"(personal identity)的問題,西方哲學從古至今有大量的討論。作為簡介, 可以參考 Eric T. Olson, “Personal Identity,” The Blackwell Guide to Philosophy of Mind, eds. Stephen P. Stich and Ted A. Warfield (Oxford: Blackwell, 2003) 352-368. 《荀子.解蔽》。 當然,當面對抉擇或者人生困難時,有些人寧願放棄自主,反而希望別人為自己做出決定、 自己只要遵從就好。我覺得這種情況其實並不構成人追求自主的反例,其顯示的毋寧是人對未 知的恐懼和對責任承擔的逃避。不過相關問題牽涉甚廣,本文對此未能仔細探究。 58 59 60 61 62 “養心莫善於誠"。所謂“養心"當然就是持養“心"作為“形之君"、“神明 之主"的地位功能。然則“誠"恰恰就是促成人自主、自我主宰的關鍵修養工夫。 我們亦曾指出,“誠"所涉及的“守仁"、“行義",既是由“君子"邁向“聖 人"的修養工夫,亦是“守道"工夫,其重點即在於使“心"“壹於道"。然而, “壹於道"和己為主宰的實質關係為何呢? 荀子認為,情欲的根本表現就是“以所欲為可得而求之",即欲望的特質就 是渴求其自身的滿足。甚至可以說,“欲"之為“欲",其內蘊就是一種渴求而 已,只不過因為對象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欲望。然而,人有“心"有“知",其必 然表現是“以為可而道之",即思量是否應該以及應該如何滿足欲望。當人“從 "、“順"性情和情欲,即當“其心正其口腹"時,“心之所可"會以當下的“情 之所欲"為標準,認可“欲"並追求其渴求的對象。在這種情況下,雖則仍有“心 之所可",但其仰賴的規範標準其實是:當下的欲望是應該滿足的。63換言之, “心"已非實質的主宰,真正主導行為的其實是情欲。之所以這是“以己為物役 ",就因為自我的行為和人生,正正受欲望及其對象所操控。 現實中,這種自我時時刻刻完全受制於當下欲望的情況,其實並不普遍。因 為人總是有自我反省的能力,總是能思考是否真的應該遵從當下欲望的指引。如 果當下欲望的追求及滿足,只會帶來好處而不會帶來壞處(包括不會減損我們可 能得到的好處) ,那麼我們或許並沒有理由抗拒當下欲望的指示。可是,現實中, 一時好欲的滿足或會帶來更多的惡果。正是基於這種認識,荀子才會提出“欲惡 取舍之權"。64“欲惡"作為一種喜歡或不喜歡的表現,固然容易察知判斷,可 是“利害"欲總是相對於其主體而言。如果我們不知道“利害"的主體是誰,也 就難以判別“利害"所在。譬如“良藥苦口",對於舌頭口腔乃至於當下的自我 而言,苦澀的藥物是厭惡的對象、是不好的,但其之所以是良藥,就因為其能在 若干時間之後,治癒身體的疾病、為那時的我帶來健康。如果所謂良藥要在千年 之後才會生效,又或者我在下一刻就會死去,那麼這苦口的藥物就只有害而沒有 利。又譬如“甲之蜜糖,乙之砒霜":同樣一杯清水,對於乾渴之人不啻於甘露, 可是對於飲水過度、急性水毒症者,卻可能是致命的。 顯然,思慮所及的對象、主體為何,就會對“心之所可"的判斷有根本的影 響。如果“心"以養一指為利之所在,卻“失其肩背",這就是孟子口中的“狼 疾人"。65如果“心"視當下情欲為根本,那就是荀子所說的“其心正其口腹" 這個陳述是受了 Christine Korsgaard 的啟發,她認為一個人(person)即使行為放浪(wanton), 但仍會遵從理由,不過其以當下的欲望為理由。參見 Christine Korsgaard, The Sources of Normativ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99, esp. 99n8. 《荀子.不苟》。 《孟子.告子上》6A.14。 63 64 65 的“小人"。66又譬如有人視藝術為畢生志業,那麼其“心"或許就會認可為了 67 藝術可以不惜拋家棄子。 再譬如君子追求以“仁義之統"為核心的“全盡"之 學,待其“積善而全盡",則更會視之為人生最高規範原則,一如荀子所說的“權 68 利不能傾也,群眾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 這樣看 來,思慮的對象不應該限於一時一地的情欲,也不應該限於自我的一部份(無論 是一指還是形軀) ,而就應該以“己"為目標。如果以外在於“己"的事物為目 標,或者僅僅以“己"的一部份為考量,其實都是置整全的自我於不顧,並很可 能役使整全的自我。那麼,核心的問題其實就是:“己"是誰,整全的自我涵蓋 和包括什麼?這個問題其實可以分成兩個部份:第一,“己"的空間和時間向度 為何?第二,“己"的內容為何? 在一般情況下,“己"的空間向度很容易確定:一個人擁有相對固定的、有 別於他人他物的身體,這個身體即構成了“己"的物理和空間存在。在日常生活 中,“己"的時間向度也不是太難確定:自我並不限於一時一刻,而是在時間中 伸延存續;在一般理解中,其存續始於出生,終於死亡。這種在時間中延續的自 我,既繫於記憶精神的相通關聯,也繫於身體形軀在變化中的持續存在。何以片 斷的人生、割裂的自我不能成就一己主宰?我們的回答是:自我既然是在時間中 存續的物理和精神存在,則一如一根手指不能代表我的身體,一個片斷的人生也 不能代表我的整體一生。假設某一時段的自我堅持其是一個整全的個體,並因而 認為其和其他時段的同一人並無內在關聯。然而此人實際上是跨越一生的物理和 精神存在,並因而有種種身體和精神的延續,以及和他人他物有種種關係。某一 時段的自我如果堅持其存在只限於該時段,則其不可避免地將面對種種認知和行 為上的困難,包括各種不協調和不一致。譬如,這個時段的自我將如何理解自己 的出現和來歷?將如何理解和面對已有的各種知識、能力和習慣?又將如何理解 和面對已形成的各種人際關係、責任和期望?另一方面,這個時段的自我也將不 可避免地影響未來的人生。如果其所做的決定和行為只著眼於當下的時段,則其 很可能會敗壞未來的自我、為未來的一生帶來各種負面影響乃至傷害──該時段 的自我或許會花光積蓄、狂歡渡日、行事不計後果,因為對其而言,其存在只限 於該時段,未來的日子既和其無關,自亦非其責任。可是,其未來的自我不免會 埋怨其行為,並會覺得受到了不公平的對待,因為其無可奈何地承接了一個破敗 的人生。如果各個時段的自我各行其是,各不相認,則這或可稱之為一種跨時域 的多重人格障礙(現在多稱之為解離式身份障礙,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 。 如果只有一個時段任意妄為,則其是對其他時段行使暴虐,因為其並沒有認真對 待在其之前和之後的人生,並沒有尊重未來自我應有的機會和幸福。69在這種情 《荀子.榮辱》。 就曾以高更 為例,探討高更拋家棄子的對錯是否和其最終成就 有關。見 最後一段引文來自《荀子.勸學》。 Thomas Nagel 曾經詳細討論審慎(prudence)的合理性,並指出其基礎即在於視一生的各個時 66 67 68 69 Bernard Williams (Paul Gauguin) Bernard Williams, Moral Luc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20-39. 況下,片斷的人生或許可以成為該時段的主宰,卻不能真正實現一己主宰,因為 其並沒有著眼於整體一生,也因而不能實現以整體一生為載體的整全自我的一己 主宰。 對於個人而言,“己"應該是整合一生、整合肉體和精神、整合性情和價值 的整全自我。一己主宰只能是這個整全自我對於自身的掌握和指引。任何一部份 的專橫獨斷,無論其是一根手指、形軀、情欲、還是片斷的人生和自我,都只會 帶來暴虐和異化。換言之,一己主宰的根本條件是自我的整合。然而,自我該如 何整合呢?整全自我又該涵蓋多少內容呢? “己"既然指涉由出生到死亡,自身在形軀和精神兩方面的持續存在和變化, 那麼“己"的內容似乎就應該涵蓋其間一切發生於其形軀和精神上的活動和經 歷。可是,即便是對於一位接近走完人生歷程、行將逝去的人來說,其一生的各 種經歷都不一定全部被視之為自我的內容──譬如某一次他夢遊其間做下種種 奇怪行徑,恰巧被家人目睹並事後告知;又譬如另一次他暴怒之下痛打好友、事 後卻自覺匪夷所思並深感內疚;再譬如他曾有一段放縱墮落的日子,酗酒吸毒、 縱情聲色,事後回想既覺記憶模糊、如陷夢中,又深覺往事不堪回首。這些經歷 大體可以視之為發生於自我生命、卻不被認為屬於自我所為。必須承認,這種發 生/一己作為的區分有種種模糊之處,亦涉及甚多爭議。我們只是希望指出:即 使是針對已經發生的經歷,從自我的觀點做出回顧,亦涉及認可或者不認可的問 題,並因而影響該經歷是否被視為自我的一部份。也就是說,“己"的內容並非 一個描述式的問題,其並不能通過外在觀察而得到完滿回答,而必然涉及自我的 認可和判斷(雖則自我並非唯一的當然權威,因為這種認可和判斷有可能出錯) 。 70 這種認可和判斷,可以稱之為“自我詮釋"(self-interpretation)。 自我詮釋既是一己對於過去以及當下自己的理解,也同時涉及對於未來的期 許,包括了我應該成為一個怎樣的人、當面對某種狀況時我應該如何反應抉擇等。 換言之,自我詮釋也並不僅僅是一種理解式活動,而同時是一種自我構建的活動。 對於一個尚在經歷人生、尚有相當年歲存活的人來說,“己"的內容既有大體已 成事實的一部份、即我的過去和作為,卻也有一個開放的未來。我們希望自我主 宰並且主宰一己人生,當然就不是等待人生已成過去,然後才去總結我的整全自 我為何,並接著才去判斷我的福禍利害為何、以及什麼是恰當的作為。我們其實 段為同樣真實,並有同樣的重要性。見 Thomas Nagel, The Possibility of Altru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25-76。 “Self-interpretation”這個概念來自 Charles Taylor。可參見 Charles Taylor, “What is Human Agency?”Human Agency and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15-44; Charles Taylor, “Self-Interpreting Animals,” Human Agency and Language 45-76; 以及 Charles Taylor, Sources of the Self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esp. 3-52。讀者亦可參考新近 一篇文章對於 Taylor 理論的回顧及討論:Kenneth Baynes, “Self, Narrative, and Self-Constitution: Revisiting Taylor’s ‘Self-Interpreting Animals,’” The Philosophical Forum 41.4 (2010): 441-457。 70 恰恰是在行進中的人生中,根據我們對於已往人生的回顧,理解自我的根本所在, 再以之指導我當下及未來的行為。也就是說,雖然我的整體一生尚未完全展開、 我的整全自我尚未完全成形,當下的我卻應該以某一種對整體一生和整全自我的 理解,來判斷、思慮和行動。這樣一種自我理解當然不可能、甚至不應該是鉅細 無遺的,未來必然有其開放性和各種可能性。這種自我理解也不需要是一成不變、 毫無修正的可能,恰恰相反,隨著不同的經歷和更深入的自我瞭解,我大有可能 修正、甚至大幅更動我對於自身的理解。換言之,成就一己主宰所必需的並非某 一種特定的自我理解,而是具備一種對於整體一生和整全自我的理解,並以之指 引人生。我們也需要釐清:當我們說“指引人生",我們並非建議、鼓吹以某一 種僵化的自我理解,無時無刻地緊張關注人生。自我理解之於人生,更多的是一 種背景式的瞭解,在慎重思慮才需要認真考究推敲,其他時候則無必要時時記掛 在心。我們希望強調的是:自我主宰其實是根據一種自我詮釋中的自我,指引人 生,以此建構一個有關聯、有意義的整體人生,並從而成就一個內在連貫的整全 自我。 五、道和整全自我 我們之前己經提到,荀子所說的“役於物"、“以己為物役",其實就可以 理解為跨時域的整全自我,被一時一地的外物乃至情欲所役使。譬如一位吸毒者 在毒癮的驅使下,不情不願或者心甘情願地吸食毒品,71當毒品帶來當下的快感 時,其吸毒的欲望得到滿足,甚至該位吸毒者在當下或也是自覺滿足的。但我們 會認為這位吸毒者被毒品役使,人生不得自主。即便那位吸毒者在該時該地萬分 情願地吸毒,甚至其或會自以為有了毒品並吸食之,他就是一己命運的主宰,但 我們仍然會認為其不曾“重己役物"。這是因為吸毒為其人生帶來種種負面乃至 破壞性的影響,其人生被毒物所操控而不由自主。同樣的判斷也適用於情欲及其 滿足。如果只追求當下情欲的滿足而不顧及其長遠的利害禍福,則是以一時一地 的滿足役使跨時域的整全自我。我們認為,荀子所說的“欲惡取舍之權",其實 就是通過“前後"、“兼權"等考量,以整體一生和整全自我的向度,來衡量“欲 惡"、“利害",並做出取捨。儒學以“仁義"、“禮義"為核心的修養工夫, 當然不可能顧及每一個具體人生的所有具體內容以及其相關取捨抉擇,其關涉的 必然只是所有人生所面對的共同問題以及各種人生將會面對的各種類似場域和 情景。譬如各種禮節就是通過養生送死等生命情景呈現一種理想的價值人生以及 相對應的德性培養。至於儒學修養最根本的原則,當然就是“道",特別是“人 道"。我們認為,“誠論"所說的“養心莫善於誠"以及相關聯的“壹於道", 其實就是根據“道"以建構整體人生和整全自我。 這位吸毒者在該時該地到底是認可吸毒並因而心甘情願,或者是不認可吸毒但無法抗拒毒 癮,這對於其行為的判別乃至評價當然有很大區別,但這兩者的區別對於我們當下的立場和命 題並沒有大的影響。 71 現在我們可以綜合說明,“誠"、“道"和建構整全自我的關係。情欲雖然 可以操控“心",使“心"“從"、“順"“情之所欲",但情欲本身,嚴格而 言只存在於當下,即其感知活動只適用於當下,而無法跨越時域地持續存在。形 軀雖然可稱之為持續存在,其本身卻沒有意識,更無法構建價值。真正能持續存 在,並構建意義價值的,其實只有“心"。荀子雖然沒有正面論述“心"的持續 存在,但他在討論“心"的“虛壹而靜"時,提到“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 72 也者,臧也。" “臧",楊倞已指出通於“藏",並認為是指“心"有所包藏。 73 冢田虎則指出“志"指“記",“言人有知而有所記憶"。 顯然,荀子已經清 晰認識到,“心"能夠知曉事物,並能夠以記憶、知識的方式將種種“知"收藏 起來。荀子對於“心"的這種瞭解,其實已經預設了“心"能夠持續存在。另一 方面,同樣是在論及“虛壹而靜"時,荀子指出“心"可以整理、統合認知:“心 生而有知,知而有異;異也者,同時兼知之;同時兼知之,兩也;然而有所謂一; 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壹。"荀子雖然提到“同時兼知之",但他指的應該是“心 "能夠同時持有不同的認知。至於認識、知曉不同內外事物的具體過程,則應該 發生於不同時段。如是,“心"的“同時兼知之",其實已經是一種初步的編排 統合,即將不同時段、不同面向的認知同時收藏於“心"。但更進一步的統合整 理則是將不同的認知納入於同一個認識體系:“不以夫一害此一"指的是互不妨 害,但兩種認知既要“兼知之",又要互不妨害,則必然不可能完全割裂獨立, 而是統攝於更高階層的認識體系,從而使得不同的認知能夠各得其所而又不相妨 害。事實上,荀子所說的“壹",應該就是指這種統合為一的工作。 其實, 《荀子.解蔽》的核心論旨就在於指出“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 大理。"“解蔽"就是解除一端之曲說所帶來的遮蔽,使人認識到不同的認知都 只是“體常而盡變"的“道"之一隅,而只有“壹於道"才能無遮蔽、不失陷。 我們之前已經嘗試論證,“誠論"所述,其實就是通過“誠心守仁"和“誠心行 義"的“養心"工夫,使得“心"能掌握“仁義之統",從而能“壹於道"。從 構建整全自我的角度來看,“養心"和“壹於道",其實也就是以“道"來整合 認知和自我行為,從而構建一個前後相聯、內外貫通、表裡如一的自我。“虛壹 而靜"是“知道"的工夫,但其所呈現的“道"的兼容並包、“體常而盡變"的 特質,其實也適用於“守道"的“養心"工夫。“養心"就是通過掌握“仁義之 統",一方面能確立愛己愛人的“教化"之“仁",另一方面又能“以義變應"。 我們認為,“仁義之統"其實也就是整全自我的基本結構。 “己"是有別於他人他物的“我"的整體,即“我"的肉體和精神。自我則 更強調“我"的精神面向,特別是精神對於自身的瞭解和認識。“我"作為一個 《荀子.解蔽》。“人生而有知",陶鴻慶認為當作“心生而有知",見王天海:《荀子校 釋》,頁 849-50。不過無論是作“人"還是“心",都不影響文本所論述的心之能力這一主 旨。 王天海:《荀子校釋》,頁 849。 72 73 肉體和精神的存在者,首先並且也是最主要的關注,就是如何在形軀和精神兩方 面生存下去,簡言之即應該如何生活(How should one live)。當我們問“應該如何 生活"時,我們關注的並不是一個技術性的問題──即我們並不是已然清楚明瞭 生活的方向和目的,尋求的只是各種手段以達成目標;我們關注的恰恰是生活的 方向和目的,尤其是生活的意義和價值,即我們探尋的是一個規範性問題──我 們希望知道,如何生活才算是好的生活,怎樣的存活才是有意義、有價值的人生。 74 荀子雖然不曾明白提出“應該如何生活"這個問題,但荀子乃至整個儒學, 關注的其實恰恰是人應該如何自處、生活的問題,即個人和群體的意義和價值追 求。75上文提到,“禮義"是“道"及其實質內容“仁義"的實踐,然則“禮" 代表的就是價值規範在實踐中的體現。《荀子.禮論》論及“禮"的起源在於以 合理的方式“養人之欲",並且強調“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別"。“養人之欲 "特別強調滿足人生而有的種種自然欲求,然則“養"主要對應的是人的生理面 向。“別",荀子解釋為“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76表 面看起來,“別"說的是人與人之間的差異和不平等,然而我們必須留意文本句 末所說的“皆有稱者也"。筆者認為,“稱"才是“別"的核心意義,即對於人 不可避免的各種差異給予相對應的對待。 荀子曾經解釋先王如何根據人的差異制定禮義:“故先王案為之制禮義以分 之,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 然後使穀祿多少厚薄之稱,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77荀子認為“群居和一"是 不同的人互相合作,而這就需要對不同的人給予不同的對待,使得其“各得其宜 "。荀子也曾說:“聖王財衍以明辨異,上以飾賢良而明貴賤,下以飾長幼而明 親疏。"78所謂“財衍",是指通過文本上一句所說的“重色而成文章,重味而 成珍備"等有餘富足之物來辨明差異,但“明貴賤"的意義在於“飾賢良", “明親疏"的用意在於“飾長幼"。“飾"和“明"都是為了彰顯“稱"和“宜 這裡提到的“有意義、有價值"並沒有預設某種特定的意義和價值。我們希望指出的是,當 人追問“應該如何生活"時,他/她總是希望過一種好的而不是壞的生活。至於什麼謂之“好 "、什麼謂之“壞",則或許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而到最後我們也不一定能達致完全統一、 客觀的答案。這裡的“有意義、有價值"在內容上其實就等同於“好",不過為了避免讀者誤 會“好"指一種淺薄、庸俗的生活(譬如吃得好、穿得暖),我們特意強調“好"的生活其實必 然涉及意義和價值。雖然我們不能直接回答“好"的具體內容,但接下來我們將會指出,“好 "的生活的一個結構要素,就是自我主宰。 譬如《論語.子路》13.9,孔子“庶矣"、“富之"、“教之"的三步驟,其實就反映了儒 家對於民眾生活的價值取向。《孟子.梁惠王上》1A.3,“養生喪死無憾"、“謹庠序之教,申 之以孝悌之義"也是一種對於民眾理想生活的期許。《荀子.禮論》的“生、人之始也,死、人 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也可以視為對人生的一種價值追求。 《荀子.禮論》。 《荀子.榮辱》。 《荀子.君道》。 74 75 76 77 78 "。荀子也曾說“爵當賢則貴,不當賢則賤"。79雖然這一句中的“貴"、“賤 "是相對於“爵"之當不當而言,卻也可以看出“貴賤"的意義在於“當"相對 應的情況。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別"其實是對於各種差異的合宜處置,亦 即對於差異的一種價值辨別。 這種價值辨別最明顯的例子,是荀子所說的“夫禽獸有父子而無父子之親, 80 有牝牡而無男女之別。" “父子之親"和“男女之別"都屬於荀子所說的“辨 "、“分"和“禮",亦即“君子"所好的“別"。觀乎其和禽獸行為的差異, 則其主旨不在於做出描述式的區分,而在於對差異做出對應的價值標識。“父子 之親"是對於“父子"的恰當價值表現,“男女之別"亦是對於“牝牡"的恰當 規範反應。然則“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別"就是說君子在滿足了人的生理需要 之後,亦追求各種價值規範,特別是能夠使人“群居和一"的價值規範。那麼對 於“應該如何生活"這個問題,荀子的答案應該是:通過禮義滿足生理需要,同 時追求在群體中的價值生活。不過,這個答案和構建整全自我的關係為何呢? 首先,我們需要釐清:構建整全自我並非人生唯一的、甚至不是首要的關注。 人類生命首要的關注是活一個美好的、有意義價值的人生。可是,一個美好的、 有意義價值的人生卻離不開一個整全自我。一個割裂的、內裡互相衝突的人生, 又或者一個喪失自我、自我被奴役的人生,是否真正是“我"的人生都成疑問, 更難談得上是美好人生。換言之,整全自我是美好人生的必要條件,雖然其並非 充份條件。或者說,整全自我是對於“應該如何生活"這一個問題的部份關鍵回 答,而不是反過來說,“應該如何生活"只是為了成就整全自我。其次,整全自 我並非外在於人生的獨立幽靈,自我也並非偶然依附於某一個人生以呈現自己。 恰恰相反,自我不過就是某一個人生的主體,其全部內容也就是這個人生的經歷 和感受,以及對於這些經歷感受的反思反省。甚至可以說,自我並非神秘的實體, 其不過就是從第一身的角度,經歷感受、觀照反省、乃至掌握主導當下的人生。 81 換言之,整體人生和整全自我其實是一種表裡關係:某一個人生之所以稱得上 是一個整體人生,是因為其有一個統一的主體,並且是由這個跨時域的整全自我 過活著;而整全自我也不過就是這個人生的主體,是經歷感受、反思反省著這個 人生的自我意識。當然,由於自我有失陷、被奴役的可能,自我意識也有可能割 裂乃至不運作,自我也不能完全等同於人生。我們強調的,只是自我和人生之間 的緊密關係。既然整全自我是整體人生的統一主體,那麼構建這個整體人生的基 本結構,乃至使得這個整體人生美好、有意義的規範價值,其實也同時就是構建 整全自我的基本結構和規範價值。 79 80 81 《荀子.君子》。 《荀子.非相》。 這種對於自我的理解,部份受益於 David Velleman 的相關論述。見 J. David Velleman, Self to Self: Selected Essay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170-202. 六、養心莫善於誠 通過禮義滿足生理需要,同時追求在群體中的價值生活。這不僅僅是對於 “應該如何生活"的答案,同時也是構建整全自我的基本結構。一般的生物,特 別是低等生物,只是憑著本能生存活動。人類有自我意識,能夠反省反思,因此 能夠超越自然本能,思考應該如何生存活動。“心之所可"就是這樣一種反思和 判斷程序。“欲惡取舍之權"則是“心之所可"所應該依從的一種標準。可是, 要做出取捨,我固然要知道當下的欲惡,卻也必須考慮未來的欲惡,以及相關聯 的,當下及未來的利害。因此,“心之所可"不可避免地需要訴諸一種自我理解。 這種自我理解固然包括對已有人生及其經歷的詮釋理解,卻也不可避免地要訴諸 一種對於未來人生和自我的期許。這種期許既是對於未來人生的理解和展望,也 同時是對於未來人生的主體──“自我"的理解和展望。 不同人生的實際內容當然會因人而異,但我們關注的是一個美好人生的基本 結構。荀子認為,這種基本結構有兩個互相構成的重要元素,一是滿足人生的各 種欲求,二是追求人生的倫理價值。之所以說這兩者互相構成,是因為各種欲求 只有通過倫理價值才能得到合理且有效的滿足,也是因為這些倫理價值恰恰是通 過人生的種種欲求和情感來展現。譬如通過衣食住行來展現恭敬辭讓,通過養生 喪死來展現敬始慎終,通過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來展現孝悌愛信。現實人生的欲求 因人而異,其倫理價值的展現也會因處境、經歷等等因素而有所不同。但荀子之 所以認為“禮義"和“仁義"就是美好人生的基本結構,是因為他相信“仁義" 和“禮義"是文理隆盛的表現,是基於對人類普遍特質和生活的瞭解,經文化累 積而成的價值規範。這些價值規範並非自成一個生活領域,獨立於生活的其他面 向;恰恰相反,這些價值規範不過就是規範如何生活的價值典範和諸種德性。譬 如仁義禮智、恭敬忠信等諸種德性,其修養和實踐並非一種神秘獨立的道德工夫, 而不過就是從德性的觀點慎思、踐行日常的生活。“仁義"和“禮義"作為美好 人生的基本結構,其義涵就在於從“仁義"和“禮義"的觀點踐行人生,使之有 意義、有價值,並成就美好。 荀子曾經描述小人和君子行事的不同: 小人也者,疾為誕而欲人之信己也,疾為詐而欲人之親己也,禽獸之行而欲 人之善己也;慮之難知也,行之難安也,持之難立也,成則必不得其所好, 必遇其所惡焉。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己也;忠矣,而亦欲人之親 己也;脩正治辨矣,而亦欲人之善己也;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 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惡焉。是故窮則不隱,通則大明,身死 而名彌白。 82 82 《荀子.榮辱》。 君子以忠信行事對人,亦可期待他人信善己身。小人行事誕詐,卻希望他人對己 親信。君子的德性人生易慮、易行、易持,並且往往能夠達成生活的追求和目的; 小人的詐誕人生需要千般計慮、萬般掩飾,卻往往難逃機關算盡一場空。所謂“人 道",其實就是以符合人的尊嚴和價值的方式過自己的人生,並也和其他同樣有 尊嚴和價值的人們一起過活。所謂“仁義",也就是以愛己愛人、合宜合理的方 式待人待己、思慮行事。荀子認為,“禮義法度"就是聖人“積思慮、習偽故" 後所制定的合乎“人道"的規範,其既能使人“群居和一",也能使個人“莫不 83 騁其能,得其志,安樂其事"。 “仁義"和“禮義"通過合理地滿足欲求、通過人生價值的彰顯,給予了人 生一個合理的基本結構。這個基本結構既是個人用於思慮行事的框架,也是關聯 一生,使得人生整全和統一的框架。這個基本結構同時是整合自我,使得過去、 現在和未來的自我有統一性的框架──其提供了一種對於人類性情以及“人之 所以為人者"的基本理解,當這種基本理解和個體生命相結合時,也就為自我理 解提供了一個基本框架。譬如當我理解到人類生命是有限的、是有始終的,而事 物有“在我者"和在於時命的區分,並且欲惡利害並非僅限於當下,而同時向未 來伸延,我乃能不耽溺於當下情欲的滿足,而是慎重地選取我的志業,並用誠懇 務實的態度追求自己的理想,卻也不忘在過程中適當滿足自己的各種生活欲求。 又譬如當我學習並踐行仁義忠信,我乃能逐漸理解和體會這是一種尊重愛護自己 和他人的生活方式,並能藉這些德性享受真誠和美好的人際關係如親情、愛情和 友情,我於是能肯認並期許這應該是我的生活方式和態度。當某一天我面對誘惑 和抉擇時,我能以這種整全自我的理解和期許思慮和取捨,放棄當下即時可見的 情欲和金錢滿足,堅守我對於親情、愛情、友情甚至道德尊嚴的肯認。 因此,“仁義"和“禮義"作為整體人生和整全自我的基本結構,並不是取 代每一個人所有的具體人生經歷、感受和追求,而是以價值規範指導每一個人去 合理地安放自己的人生並構建自我理解和期許。“誠心守仁"和“誠心行義"就 是將“仁義"貫徹於身心,使之和自我生命相結合,並因而能成為指導亦是整合 自我生命的價值規範。當“仁義"成為自我理解和自我生命的框架時,我就能圓 滿地以“仁義"轉化自然性情,並將之“形於動靜",亦更能“以義應變"。既 然“仁義之統"成為貫通我生命的統合之理,我的“心"自亦是“壹於道",即 “心"以“仁義之統"這個一貫的原則框架來思慮、取捨、行事。“誠"可以成 就以“心"為核心的整全自我,這也就正是荀子所說的“君子養心莫善於誠"。 83 最後一段引文出自《荀子.君道》。
© Copyright 2026